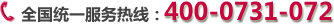
如果没有被“耽误”的十年,程钢或许早就回了国。2022年11月,46岁的他辞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终身教职,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受聘工学院特聘研究员。
出走二十载,归来已是生物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尤其在解决世界级难题“生物垢”方面,程钢有多项美国和国际专利。但不为人知的是,在科研的马拉松上,光是找对自己的跑道,明白自己适合工科而非理科,他就用了十年。

走对“道”后,程钢进入快跑模式。博士毕业后的第6年,38岁的他就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早期职业生涯奖(CAREER Award),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授予青年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回忆那十年的“沉默成本”,程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近日热议的关于扭转“工科理科化”现象的呼吁也有一些看法。在他看来,不光在课程教学体系上不同,传统的工科和理科对科研思维模式的训练也有很大不同,应该促进多样性,避免同质化。
《中国科学报》:你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0年,并获得美国知名高校的终身教职,为什么选择回国?
刚出国时,我是打算毕业后回国的。但是我的学习过程比较曲折,毕业后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看看能不能在美国这个竞争最激烈的环境中获得一个教职,加上后面孩子上学等原因就推迟了回国。
现在回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生物材料领域做了十几年,有了一些积累,已能接近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又面临产业升级。我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能解决实际应用难题的东西。
总之,这是一段新的路程,我也一直想着有一天要回来。有时候命运也是一种巧合,刚好就在这一段时间点发生了。
国外很多学校或者院系都比较小,大多数老师都是独立的。我很喜欢这种独立的科研团队,每个人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有兴趣的话大家一起合作。西湖大学的科研环境和我的偏好比较吻合,所以就选择了这里。
回来这几个月,一切都非常顺利,完全让我超乎想象。比如说西湖大学的行政效率非常的高,行政人员不能说24小时“待命”,基本上也是7×18个小时随时回复。
《中国科学报》:1999年从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化学工程本科毕业后,你进入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工作。为何3年后决定去美国读微生物工程的研究生?
我跟很多同学一样,考大学时并不是非常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我喜欢生物化学,但当时没这个专业,所以选了生物化工。但化工与化学一字之差,却是千差万别。
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主要是做一些化工厂、化工设施的设计和建设,但我的兴趣还是喜欢做科研。那个年代,中美在学术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就促使我去美国深造。
《中国科学报》:在美国完成微生物工程研究生后,你为什么又“跨学科”攻读化学工程的博士?
研究生那几年,虽然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导师也很希望我留下来,但我依旧是觉得没找到最大的兴趣点。微生物学更偏理科,而我本科受到的训练思维属于工科型,所以想再回工科看看。
后来我去了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碰巧遇到了我的博士导师。在这样的领域,我找到了多年追寻的、最感兴趣的东西,非常享受。

我们当时有个项目是利用工程化的菌株,加速降解除草剂,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做实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可以轻松又有效降解有毒化合物最重要的酶。这需要反复做实验来证明数据可靠和实验可重复性,但有两次酶的活性测试结果竟然差了10倍!
虽然知道实验结果差别可能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我潜意识里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即使我再把这个酶优化1000遍,性能提高100倍,但我怎么确定科研结果的准确性?
这让我很不舒服,我才意识到我本科受到的是工科训练,我的思维和性格更适合工科,用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还发现,我不光喜欢处理问题,还喜欢“创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消灭”一个东西。
实际上,这种多样性的训练对我现在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但我可能不像很多同学那么幸运,在年少的时候就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耽误了不少时间。
《中国科学报》:近日,《中国科学报》刊登了25名科学家、企业家的联合署名文章,呼吁扭转“工科理科化”的现象。对此,你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工科评价标准应该是处理问题。在工科训练中,能处理问题的东西一定是简单好用的,如果把体系做得很复杂,很昂贵,但不一定好用,最后按照其他学科的标准来评价工科是不公平的。这并不是说哪个学科更好,学科特点不同。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发达国家在制造业最鼎盛的时候,很多科学发现是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中来的,所以它的理论和应用都很强。我个人感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国力下滑,与学术界的“工科理科化”现象几乎是同步的,我不知道哪个是引起原因,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是相连的。
所以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系统。如果工科理科化,那么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会脱节,训练的学生也会脱节,无法为工业提供大量人才。

国内不像国外一样容易换专业,如果碰巧选了与自己思维和性格不太符合的专业,就需要寻找一个机会窗口,比如申请更高学历,但每次转换的时间成本还是比较高。
但是有时候,你觉得自身不喜欢,可能是不够了解,尤其是初始阶段。要尝试去了解,不能上来就说不喜欢,然后换了一个没做几天,再换一个。我也常对学生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把你引进来,你自己对一个领域有了一定积累和认识,才能更好地清楚自己更适合什么。
另外在做决定前,一定要得到充分的信息,寻求帮助,尤其是找到无私的、愿意跟你分享的老师或者同行,深入分析自己的喜好和背后的原因。
《中国科学报》:你从博士期间开始研究“生物垢”,将材料抗菌时间从10天延长到今天的6个月,用了12年。这期间,有感到煎熬的时刻吗?
煎熬肯定是有的。2017年,我们将材料抗菌时间做到了10天。后来又换到了更复杂的体系,但体系越严苛,抗菌时间越短,10天后就有5%被细菌覆盖了,这说明我们的系统失败了。我当时一直在思考原因,甚至对材料结构最底层的假设产生了怀疑,抗菌材料是不是不可能实现?
当时我还是年轻的助理教授,刚开始独立做科研,资源有限,所以就想不然先把这个材料放一放,看看能不能设计一个既杀菌又抗菌的膜,之后的新结构确实做到了这点。
资源有限的时候,路子走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时就一定要做出选择。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许在解决别的问题时,之前困扰多年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我希望学生既对自己的领域有很好的认识,还要对具体的技术有深刻的理解。我希望能帮助从他们更长远的发展道路上规划;希望能够通过充足的训练,让他们掌握科研全流程,而不是做生产线上的“螺丝钉”。
《中国科学报》:2015年,你在38岁时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早期职业生涯奖。能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授予青年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当时的课题是利用新型的抗垢导电高分子在脑机接口和生物检验测试方面的应用。因为排异现象是植入性医疗器械的一个难题,我们就想解决人机接口的生物兼容性问题。
很多有趣的工作是基于兴趣和自发的。但我觉得在写项目本子时,也要考虑这项工作对这样的领域来说有多大影响力,能解决什么问题。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能刚开始就把油烧完了,最好是在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有健康的职业生涯,对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进步都做出贡献。
还有一个要搞清楚,就是自己最想得到什么。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得到所有,可能要学会舍弃,轻装上阵。
一是最主要的抗垢材料,我们基本建构了一个抗垢材料化学库,有极大的信心做到针对不一样应用,随意构建抗垢材料。但最终的目标是建立更快速精准的材料设计原则,以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另外两个方向,一个是在核酸药物配送方面,一个是锂离子电池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得知抗垢材料还有很多有趣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十几年一直专注抗垢材料的原因。